1
上幼稚园的第一天,一个和我同样第一天上学的小班新生被娃娃车撞死了。
我们不是同部娃娃车,我没有看到死亡场面。然而,幼稚园的老师不得不跟我们谈这事,主要是为了告诫我们,从娃娃车下车后不可以绕到车后,跟其他小朋友挥手说拜拜,因为我们太矮太小了,司机先生看不到我们──很多年后,我读钢琴家顾尔德的传记,知道他因为心爱的狗被倒车中的车压死,也发表过类似的伤心感言,谓:养狗一定要养够大只的,不然容易被车辗过。这当然是胡说八道:大家都因此养大只狗,小只狗就让它去流浪吗?
据大人说,我小时候就会跟这个死去的小孩说话──说什么?我不记得了。但是直到不久前,我才意识到我跟「他」「报告」的频率,远超过我自己的想像。只要我生命中一有类似时钟指针「从一走到二」般的移动感时,我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会从心里拍电报般跟「他」说:嗨,我做了这件事。嗨,我到了这里。嗨我变成什么了。嗨。有时就只是「嗨」。
偶尔我甚至感觉「他」像《库洛魔法使》中的「可罗」一样,在我身边飘来飘去,「他」非常轻,我从来不觉得「他」有重量。
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分辨「离别」与「永别」之间的差异。
邻居的小孩来我家玩,为了不与她分别,我会让她长时间地藏在床底下不给大人发现。阿嬷的火车要开了,会发现她忽然间找不到她的皮包──这当然都是我做的好事。我以为,只要我可以留住某个人的某个东西,我就能永远留住她/他。我的这些殚精竭虑的闹剧,最后当然都在大人的威胁下,以声泪俱下做为收场。
然而到今天,我总还是比较同情在大人眼中不可理喻的小孩。小孩的痛苦与执着,都是因为,还没有人类后来社会生活所必要的「时间感」。
2
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小孩哭什么?因为母亲说现在要回家,明天再来玩。事情发生在我住处附近的公园里,我静静地观察着:母亲很好,很讲理。可是小孩的肝肠寸断也不是单纯的任性。他「现在」那么幸福,他「现在」那么快乐,将这一切硬生生地切断丶结束──这是不能理解的残忍。他的哭声在在要说的不过就是:「明天」算什么东西啊?
对小孩来说,糖果就还在他口中滚动流淌出美妙的汁液,从他口中把糖果掏出来,这是对他没有意义的攻击。从小孩的出发点出发,玩到一半不要玩,吃到一半不再吃,仍然是可怕的丶难以接受的奥秘。
3
法国电视台上的纪录片:犹太人回忆他们在希特勒治下丧失亲人的经过。一对小兄妹,妹妹最多只有五丶六岁,大约十来岁的哥哥负责找东西来给妹妹跟他两人吃。一天夜里,妹妹忽然醒来跟哥哥说,她实在太饿了,她想现在就吃面包,她不想等到明天。哥哥安慰她说,现在要努力睡着,不要想吃的,因为要是现在就把面包吃了,明天白天没有东西吃,会更难过。小妹妹或许已很虚弱了,坚持了一丶两下,也就放弃了。第二天,这个夜里饿醒的妹妹就去世了,原来她并没有「明天」。
我想没有谁比这个追忆中的哥哥更爱这个妹妹的,他希望她活得更长,他相信她也可以因为忍耐而熬得更久。但生命如此神秘,谁知道它的久,到底是多久呢?
医生曾说我阿嬷不会再有多少时间了,我于是从巴黎飞回台北,在台北待了十天左右,才回到巴黎,几乎只是把行李放好那样的时间里,就接到她去世的消息。医生竟然不是骗人的。
4
对时间存在样态痛苦地学习丶相信丶适应与不适应,自然影响了我对正义与书写的想法。正义并不抽象,它至少要让活着的人在活着时尽可能地享用。以差别待遇歧视同志,不管是在婚姻或是生养小孩上,限制同志的发展,在我看来,都是无聊透顶的。这实在不是「给」不「给」同志权利的问题,而是国家立法落后于社会自由与多元发展的麻烦。「同志权益」是所有人的权益,不只属于同志所有。「支持同志权益」与「成为同志」完全是两回事。成为同志这件事,我看比较像是成为伟大的钢琴家或独一无二的傻瓜一样,并不是想成为就能成为的。
然而书写并不只是为了这些今天已经可以命名的正义,书写者管的范围更宽一些,我们要管的其实是,每个已有了名字的正义可能遗漏的「其他所有东西」。在死亡面前。
5
在阿嬷还没有生病的更早以前,有一天,她特地把我叫到面前,慎重其事地告诉我:「妳如果不想结婚就不要结,知不知道?没有关系的。没有关系。」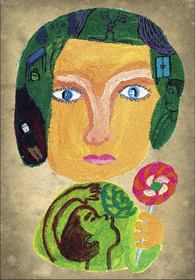 「好啦,知道啦。」我为了掩饰我被她感动的程度而狠狠装凶。她要明确地让我知道:她在乎我甚于我是什么。这种爱是如此全面:她不要妳一个闪失误会她。
「好啦,知道啦。」我为了掩饰我被她感动的程度而狠狠装凶。她要明确地让我知道:她在乎我甚于我是什么。这种爱是如此全面:她不要妳一个闪失误会她。
我知道她曾向人打听我是否是同性恋。没想到她得到的答案竟然是:「没有啦绚就是很可爱啊,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她。」(这答法使事后知情的我大吃一惊,如果我拥有如此厉害的大众魅力,我想我阿嬷一定更摸不着头脑吧)──但是阿嬷显然比大家想像的精明。
阿嬷继续问道:「像阿嬷这样的人,可以成为同性恋吗?」
我觉得好笑,阿嬷那么老了:「阿嬷妳干嘛,妳想成为同性恋啊?」
她笑了,但很坚持:「不一定。」
她跟我问了一些同性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枝枝节节,最后自己做出结论来:同性恋其实不错,她如果不是年纪那么大,她也要做同性恋。
这就是我曾拥有过的阿嬷。
这种爱是无法磨灭的。
阿嬷竟然先「出柜」。
又更早的时候,阿嬷还曾说:「阿嬷要告诉妳,爱情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。」
我问她,要说她的恋爱故事吗?
她说了对我来说一生难忘的东西:「爱情是放在心里面的。」
我阿嬷是半文盲,她的信或电话簿都要靠我帮她写。她的知识水平,在我眼中是比一般人都不足的。然而如果有所谓「爱的天赋」这样的东西,我想她是一个真正的天才。
我一向视恋爱为极端私事,亲如阿嬷,除了国中时给她看过我收到的情书(信封而非内容),我从未说起一丝一毫──我们之间,有属于我们之间的话题。这也是我跟所有人关系的原型。恋爱,是我自己成熟的过程,他人不可能代替我决定,也不需要知道太多。就像我阿嬷说的,爱情是放在心里面的。阿嬷的推测,到底中了几分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这一切都不妨碍爱的存在。
(真)爱就是,不会妨碍爱。
本文原载:《自由时报》自由副刊2011-8-10版;图:颜宁仪
18 Aug 2011
不久是多久?
阿嬷问道:「像阿嬷这样的人,可以成为同性恋吗?」我觉得好笑,阿嬷那么老了:「阿嬷妳干嘛,妳想成为同性恋啊?」她笑了,但很坚持:「不一定。」阿嬷竟然先「出柜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