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所有的愛都是一樣的,就如音樂不應該分什麼主流非主流,這不需要。有人覺得我播的音樂怪怪的,但又說不上來哪裡怪,但慢慢就會聽出它的不同滋味。這跟同性之愛一樣,愛情裡會發生太多事情。在《房間劇場》裡,我提到的很多東西都是在說尊重,尤其是對異己的尊重。跟自己不一樣的形狀、思想、行為、個性、打扮,我們是不是可以學習尊重每一個個體?」──萬芳
打開《萬芳的房間劇場》(以下簡稱《房間劇場》),屏幕裡出現一個陌生女子。這是萬芳?素顏長髮,寬大長白袍子,狀若夢游地自言自語、唱歌,氣場糾結、脆弱。
時間通道咣當作響,另一頭的萬芳,模糊得有些隔山看水。那個萬芳走在紅塵俗世間,一汪澄澈,只一首《新不了情》便唱盡天荒地老暮暮朝朝,再有《猜心》、《割愛》、《桂花釀》、《慢火車》、《溫哥華悲傷一號》,歌裡是聚散離合七情六欲。有人說萬芳不是在唱歌,簡直是在啼血。為情所困的男女,在她的呼吸吐納裡找到出口。
很久沒有聽見萬芳。自《相愛的運氣》專輯至今,已7年之久。如今的萬芳多了幾個不一樣的分身。她是音樂節目DJ,商業電台黃金時段,她舒緩卻熱烈地推介「怪怪的」邊緣音樂。她是演員,表演清單上有2部電影、8部電視連續劇、14齣舞台劇210場累計演出,成績單裡有台灣電視最高獎項金鐘獎的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,評委對她的評價是,「看不到表演的痕跡」。她寫詩,她主持,她依舊是歌手,只是在用不一樣的形式唱歌。
《房間劇場》便是一場無法定義和歸類的歌唱。2007年的女歌節上,萬芳退進一個私密的房間,用文字、聲音、肢體和表演概念性地展現自己枝微細節的體驗,她講故事、在簡單的配樂裡唱歌、窩在沙發裡發呆、蹲在地上畫蠟筆畫、學小女孩提著裙子蹦蹦跳跳、模仿女主播大聲播報新聞。故事從左手開始。天生的左撇子萬芳從小被規定要用右手寫字、吃飯,左手和右手都很沮喪,「是不是跟大家一樣就是乖呢?什麼是乖呢?為什麼花已經不在它的季節開花?為什麼愛人會寂寞?我們可不可以不那麼偉大」,一連串提問從這「左手意識」開始。以日記、書信為主軸,萬芳選取往日專輯中詩性濃厚的《飛》、《你的世界》、《迷 惑森林》、《知道不知道》等,另有翻唱經典曲目《愛之旅》、《她沿著沙灘邊緣走》和《歌》。
同性愛、地球變暖、女性體驗,萬芳用發問的方式表態,關注「少眾的、異己的、被忽略的、不被尊重的」個體,把聲音送給那些在人群裡沉默不語的「異類」。這些提問,拼湊出一個階段裡完整的萬芳。至於答案,她已在這些年的每日生活中一一給出。從下面的對話中,你或許能找到蛛絲馬跡。
我知道 說什麼都沒有意義 / 如果心已經封閉
我知道 時間不斷在遠離 / 茫然的早晨躺著寂靜
我還知道 未來不斷在靠近 / 慌亂在思緒滿溢的夜裡
我知道 假裝不會改變事實 / 如果心不是這樣
我知道 太用力就容易失去 / 愛情經不起緊握
我還知道 我會哭倒在方向盤上 / 如果一直都太堅強
我不知道 關起房門怎麼跳舞
我不知道 音樂響起怎麼開口
我不知道 脆弱時候怎麼勇敢
關于自己怎么面對
我不知道
我不知道 生活可不可以逃避
我不知道 人可不可以消失
我不知道 故事可不可以沒有結局
一個人的時候可不可以不勇敢
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知道
《知道不知道》
詞:萬芳 曲:陳小霞
「歌手是上了妝的角色,演員是卸了妝的角色。」
城市畫報:過去一年裡,有沒有什麼「第一次」體驗?
其實這幾年都在嘗試新東西,很多個「第一次」。包括持續9年在電台做DJ,做主持人,在演出裡頭擔任詩人,演戲,做演講者。
城市畫報:作為演講者,講的內容都有什麼?
從1998年開始和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有音樂上的合作,之後他們便邀請我去參加活動,譬如在9 • 21大地震、東南亞海嘯、美國卡特里娜颶風、四川地震後發起的募款。募款就是募心,希望大家發揮善念氣凝聚力量。我在演講裡會分享我跟慈濟人的相處,以及我在歌手、演員等身份中感受到的內容。萬芳這個名字有不同的身份,我把所有的角色匯整後再把感受往外傳遞。我第一次當演員是在1995年,在拍戲的過程中我有很深的感受,覺得歌手是上了妝再跟別人相處的角色,而演員是卸了妝才跟別人相處的一個角色。
城市畫報:你信佛嗎?
我不是那麼完全地懂得宗教。在所有的宗教裡頭,可能比較偏向佛教。
城市畫報:你1995年就毛遂自薦去屏風表演班演舞台劇了,那時你出到第7張專輯,當時算是唱而優則演嗎,表演最初吸引你的地方在哪裡?
只是單純有很強烈的動力想去表演,就去做了。當時唱片賣得很好,《割愛》是在我的第一個舞台劇《莎姆雷特》之後出的。在舞台劇的圈子裡,他們都叫我萬小芳。
城市畫報:你扮演的角色迥異。比如盲眼女生、生病即將離世的媽媽、排斥艾滋病人的保守者等。你如何接近一個角色?
我在《冷鋒過境》裡扮演一個罕見疾病肌肉萎縮症患者(編者注:2004年,萬芳因《冷鋒過境》中的表演獲金鐘獎最佳女主角),於是會去跟真實的患者相處,甚至把他們拍攝下來。肌肉萎縮症者越靠近心臟的地方越沒有力氣,怎麼梳頭、怎麼拿碗拿筷子、怎麼坐椅子、坐車,這都是我必須要學習的。記得我在演爬樓梯的時候,每爬一段都滿身大汗。當時感受很深,演這個戲不過是一下子的辛苦,演完了我就可以好手好腳地恢復原來的日子,可是真正的患者每天24小時都生活在這種辛苦當中。
有時候我會想念我的角色。印象最深的是《長假》,主角是一個到處打散工養家的女人玫瑰,她有一個好賭懶做的老公。有一天玫瑰發現自己生病了,日子不多了,於是她把死亡 當成自己要放的一個長假。她開始教自己的8歲的小孩學煮飯學照顧自己,她寫好12封信,托人在每年兒子生日時寄一封給他。這是我們平常生活中時常會碰到的人,一個很平凡普通的媽媽,但她有很飽滿的愛去對待家人。演戲的過程裡,萬芳和玫瑰不斷地在我身體裡對話,有時候我會進去當玫瑰,有時候我會跳出來當萬芳,默默看著玫瑰在做的所有事情。《長假》之後,我很想念她,有時候會想,不知道玫瑰現在哪裡,過得怎麼樣。
「有時候離開是為了看著自己的原型。」 城市畫報:從《相愛的運氣》至今已經7年了。當時漸漸離開歌壇是有意識、主動的嗎?
城市畫報:從《相愛的運氣》至今已經7年了。當時漸漸離開歌壇是有意識、主動的嗎?
我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歌壇,只是沒有出唱片。我也沒有離開過唱歌,唱歌對我來說並不是只有當歌手才可以做的事,我從小就唱歌,可以說我現在幾歲就唱了幾年,歌手只是某一段時間的身份。可是有一段時間我發現,作為歌手的我只能站在舞台上唱歌,反而不能唱給自己聽了,這讓我蠻傷心的。當你意識到了,就是一個轉機。所以我花了一些時間去找回那些最單純、最原始的唱歌的快樂。從2002年到現在,我一直都有唱,只是很多演唱形式跟過去不一樣,包括《房間劇場》、《房間唱遊》。我並沒有刻意離開,只是順著走。每個人生下來都有他自己的天職,或者說有他要做的功課,在那段時間,我覺得自己好像需要去做些什麼事情。
城市畫報:當時圈子裡有些人覺得你很「怪」。
有人會對我說,唱歌就唱歌嘛,就賺錢嘛,你怎麼想那麼多?但對我來說唱歌絕對不只是賺錢,所以在溝通的過程中,會有一些很奇妙的東西產生,於是便被認為「怪」。對於他們來說怪的人,可能在另一群人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。在不同的環境,大家用不同的邏輯去看待一個事情。
城市畫報:看過那時候你作為藝人上節目玩遊戲,你告訴自己「忍一下,像打一針一樣過了就好」。當時外界給你的困擾是什麼?
它會對我造成困擾的部分在於,偏偏我並沒有離開過這個舞台,偏偏我還在這個環境裡頭。我覺得唱歌不只是唱歌,還要把一些東西傳遞出去,要達成這一點我必須要有所取捨,包括跟人的接觸,要跟一些認為我怪的人接觸。這個東西會影響我,有時候我並不那麼強壯,我會覺得很沮喪、很難過、很生氣氣、很胃痛。可那只是一個過程,就像曾經有人跟我說過的一個比喻:一個女人想要小孩,她不能只想要小孩,跳過大著肚子走路,跳過飪振反應,不要懷孕的辛苦,這不可能。每個人都有他的天職,在傳遞的過程當中一定有些不容易,就是這樣而已。因為不容易,所以才要去做。
城市畫報:後來怎麼慢慢打開「不能唱歌給自己聽」的困境?
對我來說,音樂有很多種,而我們從小到大接觸到的音樂模樣都差不多。整個唱片工業都是一個模式。我從 2000年開始當DJ,可以主動去接觸所謂流行音樂以外的不同音樂人,他們打開了我對音樂和生命更多的想像。一次很深刻的接觸來自內蒙古歌手烏仁娜。她從小生長在草原,很有音樂天分,她完全不會講普通話,只會家鄉的母語,後來她到上海音樂學院學習,發現所有人進入音樂學院都用一種唱法,只是語言不同而已,所以她非常小心地保護自己來自家鄉的歌聲,直至現在。後來我和她一起回內蒙古,見到她的家人,看見她資助草原上的孩子們上學。還有客家歌手林生祥,他當年入圍金曲獎,有人通知他的時候,他正在幫媽媽養豬。這都很棒,唯有踏實地生活,才能透過音樂、戲劇等不同的渠道去傳遞。我覺得唱歌、演戲、寫詩,都只是傳遞的管道而已,它們並不是一個王子公主的遊戲,我們並不需要被大家崇拜或簇擁,不需要高高在上,我們只是傳遞者,並沒有什麼了不起。
城市畫報:你的管道源頭是什麼呢,說說你的每日生活。
我生活很簡單,只是多了一些比較細膩的觀察吧。整理房間,整理花花草草,自己做早餐,閱讀,散步,工作佔據了大部分時間。沒有工作時喜歡旅行。旅行對我來說是一種借離開對生命所做的一種反芻。早些年,我每次出國旅行,只要超過一個禮拜,就會開始做夢,夢到一些連接我原本狀態的事情,那個原本就是我在台灣所熟悉的環境。有時候我看到一些風景飛人文景觀、某些人的樣貌,都會連接回我熟悉的環境。其實這就是反芻,內容是在老環境裡無法解開的困惑或心結。在一個陌生的地方,你的名字不具有任何意義,你把自己歸零,看到自己真實的樣貌。有時候離開只是為了看看自己的原型,然後所有重要與不重要的會重新排列。 
「我總在選擇-條不是很好走的路。」
城市畫報:在《萬芳的房間劇場》的DVD開篇,你說「這不是一張快樂的專輯,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太多讓人傷心的事」,這近100分鐘的畫面和聲音算是一種療傷嗎?
我做DJ時訪問的第一個人是大大樹音樂圖像的鐘適芳,後來我們成為非常好的朋友,其實她根本不知道之前我在唱什麼樣的歌。有一次她去新加坡看我的演出,她覺得所謂流行音樂的文學化,在我身上完全表露出來了,並不單指文字,而是我所有的演出呈現裡都會加入劇場的元素。再後來她邀請我在女歌節上演出,這就是《萬芳的房間劇場》的成型。2007年5月我全然投入在《萬芳的房間劇場》裡,從零變成一部作品,全部要由我自己去發想、去創造,這個過程非常非常孤獨,有時候晚上我會被胃痛痛醒。但是另一個部分的我非常興奮,因為我們加了很多即興的東西,我想看看它最後會是什麼樣子、什麼形狀。
《房間劇場》在舞台演出結束以後,要不要出DVD這件事我掙扎了很久。我想這個東西無法是DVD,你必須到現場去感受,它非常私密,它是很多女生的故事,它是很多人的故 事,它是從我出發的小眾故事,我當時沒有辦法再演第3場第4場,它沒有辦法重複,它就 是生命當下一個很深刻的體驗,所有的眼淚所有的詮釋都是當下最真實的東西,它不是演來 的。最後有一個力量支持著我,我知道很多聽我歌的人,他們的生活不容易,在他們生命當 中,在他們的圈子裡頭,他們也是小眾,他們需要一些發出聲音的力量,而《房間劇場》如 果能給他們一些微弱的力量,那麼這就是我的心意。
城市畫報:《房間劇場》裡左手和右手的故事其實意味著對自己的認同,現在你對左手和右手的認同和解了嗎?
很多年前,在一次成長團體課程上發現左手意識,我開始去尋找它,長時間的關注點都在左手上,其實就等於忽略了右手的辛苦,它根本沒什麼力氣,但是又要做那麼多的事情。我一直覺得自己對不起左手,在籌備《房間劇場》的時候,我發現自己也很想和右手說對不起,這時候就是和解了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,我現在用左手畫圖,會直接連結到我7歲的時候,右手畫出來的線條感覺是經過訓練的,而左手畫出來的就是7歲小孩會畫的東西,很童稚。你可以用用看那只你從來沒有使用的手,你可以重新發現自己。
城市畫報:「每個藝術家的創作都是在解決一些他童年就存在的疑問」,你怎麼看這個觀點?
這個想法很有意思哦。人長大了以後,會在某個片刻聯結到自己的小時候。當我們回頭看自己小時候,會覺得自己原來那麼孤單,但其實小時候那一刻的我們並沒有那麼多的害怕和孤單,只是來來去去,正在發生而已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,有一次我回首自己的高中生活,看著自己好多年前寫的高中日記,一本一本地看,一直哭一直哭,我很想去疼惜那個高中時候的自己。突然有一只手撫摸著我流滿眼淚的臉,其實那只手是我想要疼惜高中時候的自己,很有趣的是,後來我發現其實是此時此刻的我需要被疼惜,反而是高中時候的手過來撫摸我。那是好清楚的一個畫面。小時候我很怕鬼,總是把自己縮在角落裡頭,用唱歌來壯膽,度過一整個下午。唱歌是我最深的朋友,是我一個人時候無形的朋友,所以唱歌這個事情我沒有辦法輕易對待。有時候回想起小時候唱歌的我,她可以給我很多很多的力量。
城市畫報:現場的音樂即興成分有多大?大竹研和謝傑廷的演奏,和你的演唱有時候有些互相抽離。
我們會有一個基本的架構,兩個樂器做不到絕對即興。即興的部分,譬如每一次我說話的內容會有調整,而大竹研是日本人,或許他聽不懂我在說什麼,這時候他就需要非常敏感的專注力去感受我的每一次的呼吸,我也要去融合他們的呼吸,三個人在舞台上融為一體。曲子跟曲子之間的每次彈奏都可能不一樣。我在舞台上的即興也包括每一次台下組成的分子不同,觀眾今天帶著一個什麼樣的情緒和能量進來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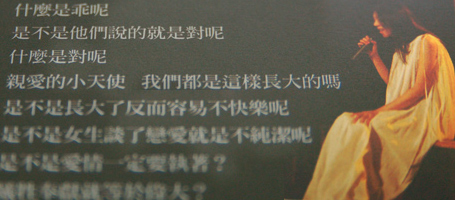
城市畫報:《房間劇場》裡講了一個有點殘酷的同性愛的故事,隨之而來的歌是林夕和黃韻玲寫的《迷惑森林》。
所有的愛都是一樣的,就如音樂不應該分什麼主流非主流,這不需要。我在比較商業的電台,把一些邊緣的音樂包裝得不著痕跡。我明白很多人的耳朵已經長期習慣了某一種狀態,強大的媒體讓人覺得音樂就應該是一個樣子。有人覺得我播的音樂怪怪的,但又說不上來哪裡怪,但慢慢就會聽出它的不同滋味。這跟同性之愛一樣,愛情裡會發生太多事情。
在《房間劇場》裡,我提到的很多東西都是在說尊重,尤其是對異己的尊重。跟自己不一樣的形狀、思想、行為、個性、打扮,我們是不是可以學習尊重每一個個體?他在這個社群裡顯得特殊,在另一個社群裡其實一點都不特殊,就像有些地方是母系社會,有些地方是父系社會,不過就是這樣而已。《房間劇場》是從小眾出發的,我本身是左撇子,在這個世界上是小眾,我是女性,在社會意義上也是小眾,我從我個人出發,延伸到對其他小眾的尊重。
城市畫報:《房間劇場》裡有一個反覆出現的疑問句「可不可以不要」,這是從對小眾尊重延伸出來的一種抗拒嗎?
這句話的前一句是「如果他們所說的就是對,那麼可不可以不要」。比如我一開始從左手變成右手,是為了跟大家都一樣,那麼大家說的就是對的嗎?如果大家說的就是對,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很多人對女人、小孩、老人的不尊重,我可不可以不要;要畫著大濃妝就叫做明星,那我可不可以不要。我經過了這麼多傳統教育、世俗教育、社會大眾輿論的教育,長成現在的我,當然知道了很多遊戲規則,但慢慢有了覺知,有了改變,也有了一些增加。
這條路不太好走,可我總是在選擇不是很好走的路,我想這大概就是我生命的意義吧,也就不會去拒絕它了。好像說這次我要做荒島音樂會,要將《房間唱遊》延伸到內地去,此時此刻對我來說是緊張的。每個地方都有它們獨特的文化、人文和思想,我不曉得到了一個新的地方,大家對房間裡的內容有什麼感覺。如果就一般來講,就簡簡單單地唱個歌就好了,何必還要傳達這麼多的東西?可偏偏我不是這樣的人,我必須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跟你們聯結。我還不知道你們的長相,你們是什麼樣的心、什麼樣的眼睛,我只能從自己出發,誠懇地去表達。讓大家在熟悉的制式環境裡,有一點不同的思考方向,我當然願意。
本文原載:《城市畫報》第236期2009年7月28日版
錄音整理:劉嘉璇(實習生);圖:大大樹提供

29 Aug 2009
萬芳·房間唱遊──左撇子的提問歌本
同性愛、地球變暖、女性體驗,萬芳用發問的方式表態,關注「少眾的、異己的、被忽略的、不被尊重的」個體,把聲音送給那些在人群裡沉默不語的「異類」。這些提問,拼湊出一個階段裡完整的萬芳。至於答案,她已在這些年的每日生活中一一給出。從下面的對話中,你或許能找到蛛絲馬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