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扔?我作勢把他扛到肩上,要往窗外拋,他哀哀求饒,又笑得喘不過氣來。你不是要我扔?
這些年幾度搬家,連衣服書籍都能丟下了,這把咖啡糖卻沒想過不隨身帶著。
那是一九九六年冬天,我在「公司」遇見了他。
那晚好冷,呼出的氣體在稀薄路燈下化成一團團白煙倏即消散,他卻穿著一條短褲,兩條腿在不聽話地打著顫,他的一雙細細的眼睛與我對望,朋友鼓動我上前攀談,好猶豫,但還是踅到了他身邊,問,你不冷嗎?他回說好冷啊你們台灣。
我意識到他不是本地人,他試著簡單交代,破碎的中文卻使得他的身世也顯得破碎:祖父一輩從金門移民印尼,他的父親在成年後曾試圖回到金門,終究與他想像中的家鄉落差懸殊,再度回印尼,結婚,生下了我眼前的他;他來台灣是為了學中文,我好不要臉地說,學中文啊,找我就好了。他嘻嘻傻笑,說自己上課會打瞌睡,唱歌學中文最有效。
他白天上課,課餘在博愛路巷子裡的旅館打工,下班都在午夜,我們的約會便從午夜開始;那年冬天很冷,我圍著一條圍巾帶著另一條,騎摩托車到他住宿的巷口等他,幫他將圍巾繫上,四處晃蕩去。
嘰嘰喳喳地他好愛說話,一會兒在我的右耳邊一會兒又在左耳,我左左右右地偏著腦袋去捕捉他瞬間便散逸在風中的聲音,有時假裝聽不清楚,啊什麼啊你說什麼再說一遍,他越湊越近,終於來到我的勢力範圍,我瞬地轉過頭去,在他臉頰上輕輕一啄,好得意。他大叫不行不行,這在我們國家會被抓的。
印尼排華,又是戒律森嚴的回教國家,他是邊陲的邊陲,雙重的流離;難怪他小心保護自己,連宿舍和打工所在都沒主動告訴我,而我,就只是等著。
多半時候我們不知要往哪裡去。我們到Funky跳舞吧,他想了想,搖搖頭;那我們上陽明山看夜景,他又想了想,又搖搖頭;那你想去哪裡呢?他囁囁嚅嚅語氣好委屈:我不知道。於是我們穿戴著夜色,一條街騎過一條街,看著燈火黯了下去又有幾盞亮了起來。
我們的關係也像這樣,我們進一步交往吧,我說;他嗯嗯地想著,可是,可是我就要回印尼去了;我說,不要去管未來了,就是現在,要不,我們退一步,否則我很痛苦。他也不願意。他在後座緊緊抱著我,取暖一般,我車子騎得飛快,沉沒在沉默裡,他唱起歌來了,攤開你的掌心/讓我看看你/玄之又玄的祕密/看看裡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,就這樣我們不進不退,徘徊在冷冷的冬天的台北街頭,徘徊在掌心裡的感情線與理智線之間,進退都有說不的理由。
春節過後他就要回印尼了。
放年假前我斷然把工作給辭了,因為一些不愉快,同時將家用電話換了號碼,卻在同時間,他也搬離了宿舍,我打電話過去,一個尖銳的女高音重複說著,你撥的是空號,請查明後再撥,你撥的是──同在一座城市裡,我們竟就這樣斷了聯絡,這是一個九點半檔俗濫至極的橋段,卻把我抓去當了主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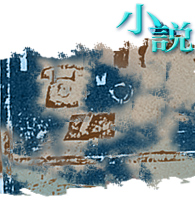
我打電話到印尼駐台辦事處、印尼觀光局等機構,又到北部幾所設有語言中心的學校詢問,他們查不到學生資料,但答應將我的尋人啟事交給印尼學生組織,回音很快到來,都說沒有,沒有你要找的人很抱歉喔,也到博愛路去一家旅館問過一家旅館,或是還不太熟練地上網登錄找人,沒有,沒有,沒有,一個曾經在我耳邊講話唱歌伊伊牙牙說著我捉弄他的「楊麗花發明非揮發性化學花卉肥料」的人,竟就像我虛構的人物,Shift壓住後用滑鼠圈出一個反白區,Delete按下,從此消失。
在他預計回印尼當天,我還是去送了他,隔著玻璃窗,我望著一架架飛機逐漸駛離視線。他就在某一個機艙裡。
從此我留心印尼的消息,好像我在一個個統計數字裡也可以分辨出他所占有的那個獨特位置,並用想像使他充滿精神。
然而這幾年來出現於報端的,多半是災難新聞,九七年霾害,九八年年中大規模排華、年底兩場空難,○一年峇里島爆炸,○四年地震加上海嘯肆虐,少則數百多則數十上百萬人傷亡,好神經質地我檢閱 著一張又一張圖片上的人物。你現在三十初渡了,鼻子尖尖眼睛細細和薄薄的嘴唇這些都不會改變;但你變胖了嗎?一定是的,唇上蓄短髭了沒?那是你所以為的性感符碼,像克拉克·蓋 博;你仍戴著我送你的那個白金手環嗎?一如我仍保留著你放在我家的咖啡糖;你在找我嗎?你知道我在找你嗎?如果你知道我在找你,為什麼你不來找我?喔,一定是,一定是你沒有我的聯絡方式了,我這就給你,我的e-mail是──我的手機是──現在我們都用手機了,我的地址是──
伊聽著聽著,唰地一下眼眶便濕潤了,我抱抱他,伊瞬間咧嘴大笑,你被騙了,可惡,你心裡原來有別人,改天趁你不在,我代你丟了這些糖果。你敢,我捏捏伊的臉頰,你啊愛哭鬼小心眼。可不是嗎,一個假日清晨伊生悶氣,我問了半天伊才說,昨晚你怎麼背著我睡,以前都是面對面的。
伊不懷好意地說,那是陰謀,一定是陰謀,不這樣你不可能記他這樣久;伊又認真問我,以後你會不會也像記住他一樣記住我?我摩摩他的腦袋瓜,說一聲傻蛋。
咖啡糖有保存期限,傻蛋,我真的不知道記憶有沒有,也許 它像傳真紙一樣,慢慢地也將褪去了顏色。走吧,傻蛋,我們吃飯去吧,我聽到你的肚子餓得咕咕叫了。
本文收錄於王盛弘著《關鍵字:台北》(2008年,台北馬可孛羅出版) 。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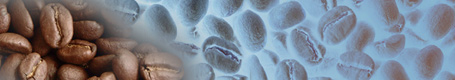
 列印版本
列印版本












讀者回應
搶先發表第一個回應吧!
請先登入再使用此功能。